“横看成岭侧成峰”——读六卷本《哈佛中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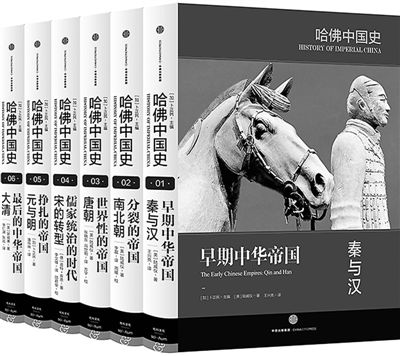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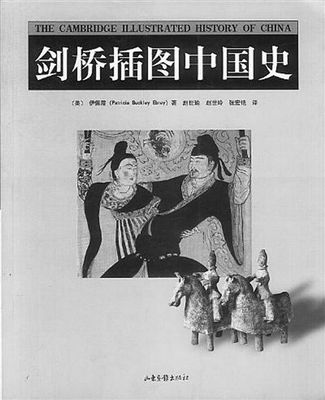
近日,6卷本《哈佛中国史》中译本上市。这套丛书由著名汉学家卜正民领衔主编,倾十年之功,可以说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最能代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著作。出版后,已被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等数十所世界知名大学指定为教材。
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其实从未停止。除了上述两套西方学者的代表性成果以外,近年来出版的还有日本讲谈社的12卷本《中国的历史》、宫崎市定的《中国史》等等,更不用提针对某个历史节点或事件进行阐释的单行本著作了。
海外的中国历史研究为何这么火?与几十年前相比,现在的研究有什么新动向?这反映出,世界看中国的眼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应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本期“书界观察”栏目综合了多位专家视角,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编 者
“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对汉学家卜正民所说的一段话。正是这段话,帮助卜正民走出迷茫,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继续一路前行。
如今,在他所主编的《哈佛中国史》序言中,卜正民反过来向中国读者发出了邀请:
“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不过,这套书或许也会引起人们的一些疑问。
海外中国通史研究著作已经出过多个版本,比如最为人们熟知的《剑桥中国史》,日本学者撰写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等等。与之相比,这套《哈佛中国史》最大的特点在哪里?
首先,最明显的当然是体量不同。《剑桥中国史》卷帙浩繁、内容专深,已有皇皇16卷,并且至今也没有全部完成。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也有12卷,中译本出了10卷。《哈佛中国史》则是6卷本。
另外,《剑桥中国史》是由多位作者合力撰写一卷,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与《哈佛中国史》都是每卷由一位学者独立完成,因此语言、文风更活泼,更流畅,更适合普通读者。
其次,选取的历史起止点不同。《剑桥中国史》从秦汉写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覆盖”式的,但也有人诟病——中国的历史,哪儿能从秦汉开始算起呢?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就是从神话时代写起的。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界也有一种不断将历史向上追溯的潮流,比如从官方推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到近年由于考古发掘而重新认识“最初的中国”。
然而,越追越早的历史也碰到一个理论与方法的瓶颈,那就是——原本“满天星斗”的邦国,什么时候才可以算内在同一的“中国”?在什么样的历史形态下,那片广袤区域才有了一个“中国”共识?《哈佛中国史》上起秦汉、下至清代,写“帝制中国”的历史,聪明地避免了有关何为“最初的中国”这样的争论。
欧美学者更习惯于专题研究,对撰写上下通贯、包罗万象的通史,向来抱持谨慎态度,特别是这半个世纪以来,欧美中国学界撰写系统的中国通史并不多。这套6卷本通史,或许可以较为全面地呈现近年来欧美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普通读者或许不解:通史著作有一套经典、好读的就够了,为什么还要不断编写中国历史呢?
那是因为,观察历史的立场、角度和方法是变动与多元的,因此,历史著作也需要不断更新。
比如20世纪以来,研究中国历史的现代史学,不仅增加了“古今”“东西”“中外”等分析框架,也用进化的观念代替循环的观念,以平民的历史代替帝王的历史,在文献之外增加了考古发掘与田野调查,对历史资料进行了客观的审视和严格的批判。
但到了21世纪,又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新观念、新角度、新方法:本质与建构、想象与叙述、后殖民与后现代、国别与区域、物质与文化、疾病与性别……这使得“中国”与“历史”不得不被拿出来重新认识。
那么,与中国学者自己的通史著作相比,海外中国史有哪些不同?
最大的不同,肯定是文化背景的差异所带来的视角、观念的不同,继而也会带来研究方法的差异。
长期以来,中国的中国通史,基本上会以政治史为主要脉络,关系到古代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在历史叙述中总是占了很大篇幅,其他领域大体依附在这个主轴上。尽管从梁启超《新史学》和《中国史绪论》开始,中国通史写作就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叙述方式,但总体变化似乎并不大。从晚清民国流行的夏曾佑、缪凤林、钱穆,到1949年以后成为主流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当然也包括各种通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大体都是一根主线(政治与事件)、若干支流(社会经济、对外关系、思想文化)。
在《哈佛中国史》中,我们则看到:当下国际历史学界风起云涌的环境气候、性别医疗、社会生活、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等各种角度,越来越多进入了历史。
例如,几乎每卷都专门设有一章讨论有关宗族、性别、日常礼仪的内容,如秦汉卷第七章《宗族》、南北朝卷第七章《重新定义亲属关系》、宋代卷第七章《人生礼仪》等等。其中,宋代卷第十二章《公共领域中的私人生活》还运用考古、图像与边缘文献讲述有关卫生、装扮、保健与福利的情况,提供了生动立体的宋代生活场景,使历史不再是严肃刻板的单一向度。《元明》卷对于“物华”即文物、书籍、家具、瓷器、书画以及欣赏品位与商品市场的描述,也是过去国内通史著作中不太常见的。
特别要提到的是环境史。众所周知,气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前竺可桢就写出了《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等杰出的论文,但除了寒冷气候对于北方游牧民族迁移和南侵的影响外,我们的通史著作并不那么注意环境与气候在政治史上的意义。而卜正民所写的《元明》一卷,却用“小冰川时代”这一因素,贯串了整个13世纪至16世纪的中国历史。尽管他所谓“小冰川时代”与竺可桢的说法有些差异,有的证据(如用明代绘画中的《雪景图》证明气候变化)也多少存疑,但是,把这一点真正有效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并作为政治变化的重大因素,确实令人大开眼界,也使得历史本身和观察历史都变得复杂化了。
海外中国史研究有什么不足之处?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卜正民曾经产生过的迷茫,或许是每一位汉学研究者都经历过的。而这种“不够真切的理解”,也许就是海外中国史最普遍的“先天不足”吧。它必然会影响到史料的搜集、取舍、引证、分析等方方面面。
仍以《哈佛中国史》为例。
首先,从文献资料上说,这套书有的部分虽然开掘了若干边缘文献,但有时不免过于轻忽主流历史文献(比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的引证,甚至有一些常见的正史文献都要从今人的著作中转引。并且,对于近年中国学界的论述较为忽略,显然对中国学者的新研究了解相当不足。
其次,书中有些论述也有不完整、不深入或者还有疑问的地方。比如《唐代》卷说“隋唐佛教最终分成了四个宗派”(天台、华严、禅和净土),就不太可靠;《清代》卷中,对于费正清朝贡体系的批评也难以服人,尤其是他举出的例子——即大清帝国和朝鲜、越南在“引渡与边界”方面“基于对等主权国家的模式”,这一说法也缺乏历史证据。
其实,任何一套通史著作,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是通史著作被不断重写的意义所在,历史不可能终结于某一次写作。
不断出现的中国历史著作,是否表明世界看待中国的目光发生了变化?对于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有什么价值?
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以及重写“中国史”背后的全球史背景。
学术史要“别同异”。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应特别注意它自身隐含的政治、学术和思想背景,千万不能把他们研究的“中国史”和我们研究的“中国史”都用一个尺码评判或剪裁。
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异己之学”,恰恰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所研究的“中国”不同,才要特别重视。如果没有这个“异”,我们还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呢?他山之石才可以攻玉,有所差异才互相砥砺。中国学者总是说“和而不同”,但往往只有“和”而缺少“不同”,或者只有“不同”却没有“和”。所谓“和”,应当是一种理解,即理解这种历史观念的“不同”。
苏东坡有一句著名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不同角度,往往观察各有所得。如果说,日本学者对中国史是“横看成岭”,那么,西洋学者就是“侧看成峰”,相信它们都会带给中国读者和研究者新的视角,引发新的思考。
(本文主要参考中国思想史学家葛兆光为《哈佛中国史》所作推荐语,本报记者周飞亚综合整理)
